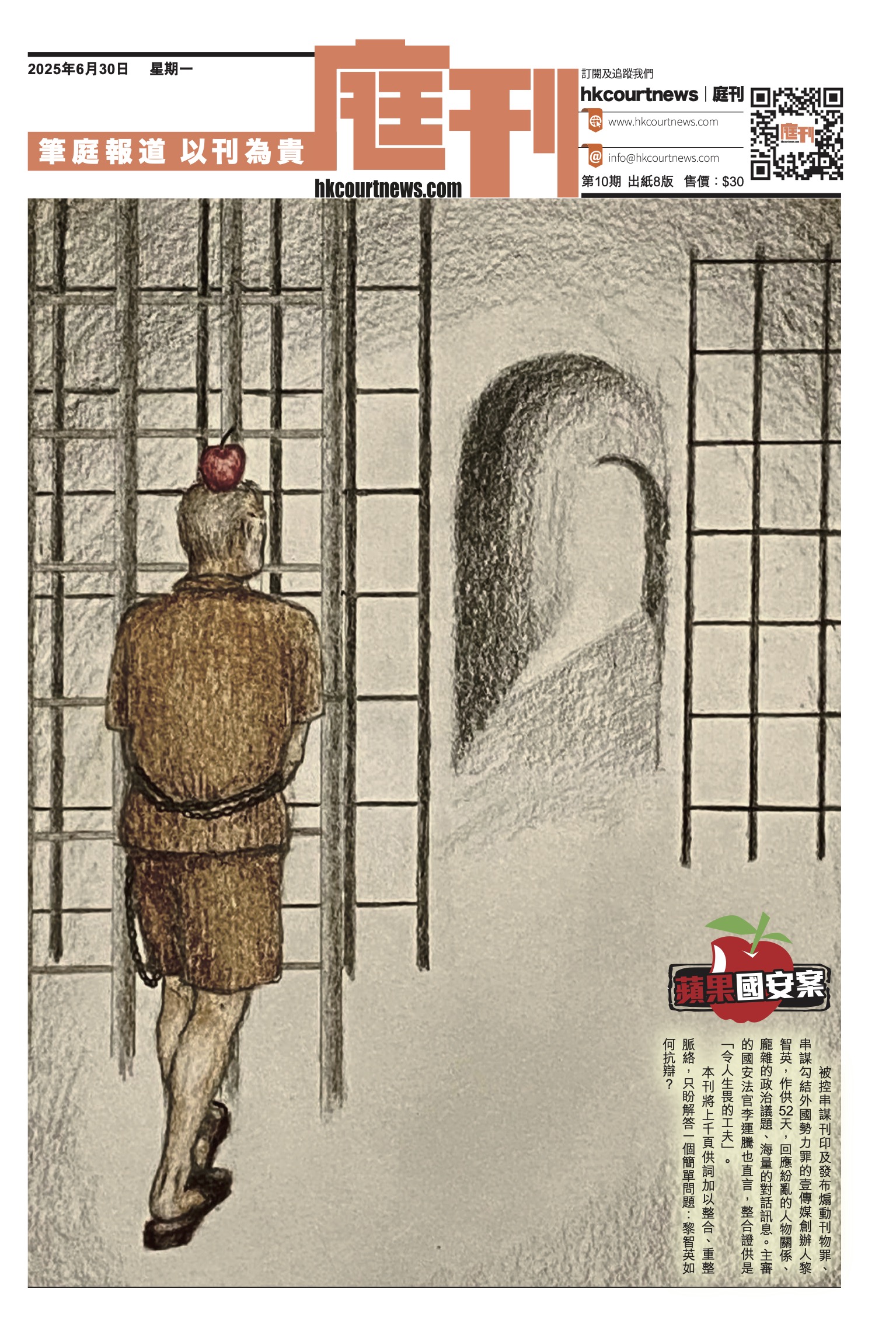報導以「如何抗辯」為主線,把黎智英在歷時52天作供的龐雜證詞與對話重新排整。主審官指整合證供是「令人生畏的工夫」。黎承認在《國安法》生效前,曾在訪美會面與撰文中提出或支持制裁構想,包括向時任國務卿蓬佩奧提議制裁打壓運動的中港官員、在外媒撰文主張撤銷官員子女學生簽證、於訪問中提出凍結中國貪腐官員海外資產與科技限制等;但他強調自己「不會打違法的仗」,《國安法》生效後已改變方式,不再請求制裁。控方則引用他法後的專欄、直播及與外國人士的對話,指其仍持續倡議制裁。黎在庭上表示會為模糊紅線冒險,但明知違法之事絕不會做;當法官問為何不遠離紅線,他答「當你要挺身捍衞自由,你就不能夠遠離紅線」,並同意自己「打擦邊球」。
時間線上,2019年反修例期間已出現國際遊說意向。2019年7月赴美前,助手轉述美方建議他提出具體可行動點;會面時他向蓬佩奧提議制裁涉打壓的中港官員,但稱未提官員子女。其後他草擬文章動員美國民眾向國會請願(最終未刊),並與多名美方人士電郵討論「馬格尼茨基式制裁」,對建議制裁個別官員的意見回以「好主意」。2020年5月,他在《紐時》撰文與在霍士新聞受訪,談及撤銷官員子女簽證、凍結資產與科技措施,同時表示不贊成「完全取消香港特殊地位」,以免削弱香港的經濟價值。然而在同年7月,他在回覆蓬佩奧助手的轉問時表示,重點不在香港而在中國,並認為在中美脫鉤的情勢下,美方撤銷香港特殊地位或屬可行;控方據此質疑其立場更進取。對於助手曾向美方建議制裁名單的訊息,黎稱不知情,亦未過問,理解為《國安法》後相關遊說等同被廢止。
被問到《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》,他起初認為作用不大,後承認自己看法有誤,並確認支持法案通過但否認遊說制裁。對於是否「攬炒」,他否認,稱香港不是被美國犧牲,而是被《國安法》的實施犧牲,又多次說「香港已經玩完」。他解釋法後的立場是以合法方式表述觀察與心情,寄望外部壓力可令《國安法》效力受限,在專欄中亦寫到取消特殊地位與制裁中共官員「或多或少」能牽制中共,讓港人感到有人「為我們出氣而寄存希望」。
法庭互動成為報導另一重點。法官屢言本案是刑事審訊、無關政治與立場,要求被告專注答問,不要爭辯;當黎自稱「政治犯」時,法官糾正他是在接受刑事審訊。庭上多次圍繞言論自由邊界作推演,法官以誹謗等例子追問「是否存在終極言論自由」,黎答承認沒有終極言論自由,但認為說錯話的人亦應受保護。關於身分認同,黎在直播舊語句被追問時稱「我們是香港人」,並在庭上與法官就「我們是中國人」一語展開釐清;法官問他「是否黃皮膚」,他回「我是黃皮膚,就是中國人了嗎?我是香港人」,次日他主動澄清自己是「香港中國人」,與其「愛國不愛黨」的說法一致。另有以父子關係比喻中台關係的提問,黎回應「孩子不可宣稱自己是別人兒子,但仍可不認自己的父親」。在被控方指出他曾言及與外國嘉賓傾談或會惹禍時,他承認知悉風險,但重申對明確違法的事不會做。
整體而言,控辯爭拗集中於三條界線:一是《國安法》前後的時間分野;二是評論、倡議與「請求」之間的語義區隔;三是言行與可罰性的認定。報導透過還原訊息往來、會面紀錄、專欄與庭上對答,呈現被告如何界定自身行為與風險,以及法庭如何在證據與提問中界畫邊界,並記錄多處引發關注的問答語句與其原貌。